您現在的位置: 百濟新特藥房網首頁 >> 肝病科 >> 新藥動態
美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處理流程詳細介紹
- 來源: 新特藥房藥訊 作者:百濟動態 瀏覽: 發布時間:2006/9/9 18:00:00
美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處理流程詳細介紹
于樂成 張欣欣 陳成偉 虞福亮 姚光弼
慢性乙型肝炎(CHB)是美國及全球重要的公共健康問題。大約25%嬰幼兒時期感染HBV的患者因肝硬化或肝癌而過早死亡。由美國肝病學家組成的專家小組此前曾制訂和出版了關于CHB的處理流程。鑒于對CHB的認識日益加深、現有的更為敏感的分子生物學診斷方法的建立、新治療手段的出現以及對獲準的治療方法的各種優缺點認識的加深,對原有的治療有進行修訂的必要。修訂以系統復習文獻所獲證據為基礎,而對于部分缺乏具體參考資料的內容,專家組主要依靠臨床經驗和專家共識進行修訂。目前,應用敏感分子生物學方法,已可檢測低至10 IU/ml的血清HBV DNA,因此臨床應確定抗病毒治療前患者的基線HBV DNA水平,監測對抗病毒治療的應答和監視抗病毒藥物的耐藥情況。抗病毒治療的首要目標是持久抑制HBV復制,盡可能使血清中的HBV DNA降至最低水平。關于適合抗病毒治療的HBV DNA閾值HBeAg陽性的CHB患者為≥20000IU/ml; HBeAg陰性的CHB患者宜降低為≥2000IU/ml;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為≥200 IU/ ml。干擾素α-2b、拉米夫定、阿德福韋、恩替卡韋、聚乙二醇化干擾素(PEG-IFN) α-2a等均已被批準用于CHB患者的初始治療,但各有利弊。選擇時需要考慮的問題包括療效、安全性、耐藥概率、給藥方法及治療費用等。
本版乙型肝炎病毒(HBV)處理流程由美國肝病學家組成的專家小組制訂,其第一版于2004年發行,此后又有兩種藥物,即恩替卡韋(商品名博路定,生產商為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和聚乙二醇化干擾素α-2a(商品名派羅欣,生產商為羅氏公司)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于治療CHB。基于對CHB自然史的新認識和上市后獲得的藥物評價資料,專家組成員再次聚會,重新評價和修訂治療建議。其目的是對先前制訂的有關美國慢性HBV感染者診斷、治療和監控的實用綜合性流程進一步增補和修訂。借助“連續性文獻復習(structured literature review)”和對現有治療指南的評估,并以各位專家的獨立調查研究為基礎,專家組對新出現的資料進行了甄別,以便綜合評估。連續性文獻復習的措施包括在PubMed電子文獻數據庫中廣泛檢索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7月28日之間出版的有關CHB治療的英文論文。此外,依據相關論文進行的手工文獻檢索以及本領域專家之間的磋商也為本版流程的制訂增添了參考資料。通過制訂明確的采用和排除標準對某一文獻的可接受度進行評估,共從455份文獻中采納了37份論文。另外還從2004和2005年的消化疾病周(Digestive Disease Week,DDW),2003和2004年的美國肝病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年會,2004和2005年的歐洲肝臟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年會論文集中選取28篇摘要作為依據。此后還從2005年AASLD年會中選取一些摘要予以補引。
在本次會議之前,專家組成員對本版流程中與關鍵決議點相對應的綜合臨床情況下不同治療選項的恰當性進行了評估。一種9分制評定量表被用來突出顯示對有關治療選項恰當性的一致或分歧意見。這種評分信息被用來探究各種分歧意見存在的原因,以幫助專家組達成共識。只要有可能,專家組根據循證醫學證據提出建議,但如果缺乏相應的佐證資料,專家組成員將依靠他們個人的臨床經驗和有關專家意見做出建議。本《流程》的目的是幫助經治醫師回答有關實際問題,包括需要作何種檢查,如何解釋檢驗結果;哪些病人需要治療;何時開始治療和治療多長時間;有哪些可行的治療選項,以及如何監測患者的病情等。在達成這些推薦意見時,并未考慮治療費用問題,因為目前尚缺乏針對所有批準用于治療CHB物的成本-效益資料
一、疾病負擔
據估計,全世界至少有3.5億慢性HBV感染者。雖然美國HBV感染的流行情況低于許多其他國家,但估計也有125萬人感染HBV。然而,美國的CHB流行情況有可能被低估。在美國以外出生,從亞洲、中東及非洲等地移民進人美國的人群中,HBV感染的流行情況從5%一15%不等,反映了他們原先所居住國家的HBV感染的流行模式。在過去的10年中,亞裔美國人數量有了顯著增長,據估計目前已有約105萬人。最近在美國數個大型城市進行的一項橫斷面調查顯示,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人群中,HBsAg的血清學流行率為10.4%。在紐約市進行的一項回顧性調查顯示,紐約的亞裔美國人中,可檢出血清HBsAg者高達驚人的23%。1990一2002年間急性乙型肝炎的發病率降低了67%,部分原因在于廣泛接種乙型肝炎疫苗。盡管如此,新發HBV感染仍然比較常見。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估計,在美國每年約有7萬人發生急性HBV感染。CHB患者發生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償及肝細胞癌(HCC)的風險增加。據估計,大約25%嬰幼兒時期感染HBV的患者因肝硬化或肝癌而過早死亡。估計在美國死于這些HBV感染相關并發癥的患者每年高達5000人。
二、自然史及相關術語
發生急性HBV感染后,大約3%一5%的成人和95%的兒童患者不能產生充分的免疫應答以清除HBV感染。這些患者將發展為慢性HBV感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乙型肝炎管理組所采用的描述慢性HBV感染不同階段的臨床術語及其診斷標準總結于表1。其他與HBV感染相關的臨床術語總結于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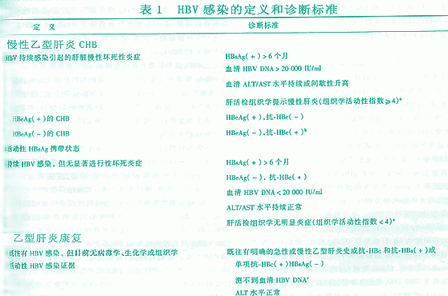
摘修自:Lok and McMahon。a:任意肝活檢標本的組織學表現;b:絕大多數這類患者在前C或C啟動子的突變;c:應用PCR法有可能測出極低的HBV DNA水平

摘修自:Lok and McMahon
慢性HBV感染的標志是血清中持續存在HBsAg、HBeAg及高水平HBV DNA。成人獲得性HBV感染的早期階段常伴有明顯的病情活動和ALT水平升高,而圍產期獲得感染者的ALT水平多趨向正常(免疫耐受階段)。后者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活動并有ALT水平升高,但通常在成人期之前不會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可自然發生,也可在抗病毒治療后發生,在ALT水平升高情況下常見。在HBeAg消失和血清學轉換之前,通常先有顯著血清HBV DNA水平下降(<20000IU/ml),并通常伴有ALT水平復常。因此,HBeAg血清學轉換通常表示由CHB轉為非活動性HBeAg攜帶狀態,后者沒有明顯的臨床肝炎證據,血清HBV DNA處于更低的水平。部分患者HBsAg也消失,而這被看成是HBV感染的康(resolution)。然而,一般情況下絕大多數CHB患者的病情可以得到控制,但并不能根本治愈。
一部分發生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可以出現HBV DNA水平的再度升高,以及ALT水平的持續或間歇性升高。這類患者體內在自然發生的HBV變異株,從而消除或下調了HBeAg的產生,其機制通常是由于前C或C啟動子區發生了變異。這種類型的慢性HBV感染被稱為HBeAg(-)的CHB。因此,CHB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形式:HBeAg(+)的CHB和HBeAg(-)的CHB 。一項對283例發生自然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的研究顯示,在平均隨訪評估8.6年后,大約2/3的患者為持續HBeAg血清學轉換;24%的患者有ALT的升高,與檢測到HBV DNA相關。
肝病活動的自發性發作(spontaneous flares)可以在CHB的自然過程中發生,反復發作病情加劇可導致進展性肝纖維化和肝硬化,并可能致癌。在相似的HBV DNA高載量及ALT正常的情況下,作為HBV慢性感染的一種結果,肝活檢發現年齡較大患者的肝纖維化很可能比年齡較輕的患者嚴重。若不給予治療,伴有HBV DNA和ALT水平升高的HBeAg(+)及HBeAg(-)CHB進展為肝硬化的比例很高。有2項安慰劑對照研究的肝活檢結果顯示,未經治療的患者在48周以后進展為肝纖維化的比例高達21%一36%。對于CHB患者,伴有代償性肝硬化者的5年病死率為16%;伴有失代償性肝硬化的患者,如果不進行肝移植,則5年病死率為65%一86%。HBeAg和HBV DNA的存在使發生HCC的風險增加。有研究顯示,與無HBsAg者相比HBsAg和HBeAg同時陽性的男性患者,經推算,其進展為HCC的相對危險度為60.2(如果僅HBsAg陽性,則相對危險度為9.6)。該項研究還提示,能夠測到HBV DNA(分枝鏈DNA分析法Quantiplex試劑盒,Chiron公司)的患者,其發生HCC的可能性為不能測及HBV DNA者的3 .9倍,且HBV DNA水平越高,發生HCC的風險就越大。
新近發布的一項對3 653例CHB患者(其中164例患者發生了HCC)的長期隊列研究發現,HCC的發病率與HBV DNA的生物梯度相關,亦即與HBV DNA水平之間呈現濃度效應(dose-response)關系。在HBV DNA<300拷貝/ml的患者,HCC的累積發病率為1.3%,而在HBV DNA106拷貝/ml的患者,HCC的累積發病率升高至14.9%。在去除了年齡、性別、吸煙、酒精消耗、ALT水平和HBeAg狀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后,HBV DNA水平與HCC發病率之間的這種生物學梯度效應仍十分顯著。另有一項相似的研究對3 582例患者進行了調查,顯示在HBV DNA<300拷貝/ml和≥106拷貝/ml的兩組患者中,肝硬化的累積發病率從4.5%升至36.2%。這種血清HBV DNA水平和肝硬化發病率之間的相關關系獨立于HBeAg狀態及ALT水平等其他變量之外。
由于HBeAg和HBV DNA均是HBV復制的標志,因此前述有關研究均提示在慢性HBV感染進程中存在病毒復制,這為通過抗病毒治療以阻止肝病的進展提供了合理依據。
三、病毒變異
HBV的變異率大約為其他DNA病毒的10倍,與其他絕大多數聚合酶相比其逆轉錄酶缺乏較常見的校讀功能。變異可以發生于HBV的不同基因片段;數種病毒變異株可自然或在抗病毒治療選擇壓力下發生。在當前的臨床實踐中,有4種HBV形式是相關的:野生型HBV、前C變異株、C區啟動子變異株及抗病毒治療誘導的各種變異株。
(一)前C和C啟動子變異株 HBeAg一般被看成是HBV復制的標志。以往HBeAg(-)被認為是無病毒復制的HBV感染。ALT水平正常的HBV感染者曾經被稱為“健康攜帶者”,但現在改稱為“非活動性HBsAg攜帶者”。為了評價其他可能引起肝炎的因素,在ALT水平升高但缺乏HBeAg的HBV感染者中進行了許多研究。20世紀80年代早期,在地中海地區發現越來越多的HBeAg(-)的活動性HBV復制患者。1989年,從有活動性HBV復制的患者體內分離的HBV基因組中發現了能阻止HBeAg形成的特殊變異。最常見的為前C區G1896A替代變異,導致形成一終止密碼子,阻止了HBeAg的合成;相應毒株被命名為“前C變異株”。其次是一種重要的雙變異,即“基本C區啟動子雙變異株”,包含A 1762T和G1764A兩種替代變異,導致HBeAg產生下調。
盡管有報道,前C變異株可以發生傳播,HBeAg(-)的CHB并非典型的獲得性HBV新感染。前C變異株最常作為典型的
野生型HBV毒株感染過程中的優勢株,在免疫清除階段(HBeAg血清學轉換)得以篩選出來。HBeAg(-)CHB的形成可以在HBeAg血清學轉換后不久,也可能在很多年甚至幾十年后形成。HBeAg(-)的CHB有2種主要的疾病活動模式。大約30%一40%的患者表現為ALT水平持續升高(升高3-4倍),但45%一65%的患者表現為ALT間歇升高并常有急性發作。血清HBV DNA水平也趨向增高,特別是在ALT升高之前。然而,HBeAg(-)CHB的平均HBV DNA水平低于HBeAg(+)的CHB。持續的自發性緩解在HBeAg(-)的CHB是不常見的,僅為6%一15%,其長期預后也不如HBeAg(+)的CHB患者,其部分原因可能是HBeAg(-)的CHB患者多為HBV感染晚期。
(二)抗病毒治療誘導的變異株 YMDD變異是發生在HBVP基因編碼的DNA聚合酶活性位點“酪氨酸-蛋氨酸-天冬氨酸-天冬氨酸(簡稱為YMDD)”的一種特殊變異。這種變異是在L-核苷類抗病毒藥物,如拉米夫定和恩曲他濱的選擇性壓力下形成的,并導致產生一種活性位點發生改變的病毒聚合酶,從而對某些特定的抗病毒藥物產生耐藥。
新近已分離出HBV逆轉錄酶中與阿德福韋和恩替卡韋相關的其他變異。阿德福韋耐藥的特征是HBV逆轉錄酶的B和D區出現A181V/T和(或)N236T兩種關鍵變異。雖然目前尚未在應用恩替卡韋進行初始治療的患者中觀察到耐藥證據,但在已經存在拉米夫定耐藥變異(I169, T184, S202, M250)的患者中發現了對恩替卡韋的表型耐藥。
四、HBV基因型
根據HBV S基因序列相差4%以上或全基因組序列相差8%以上,目前可將HBV劃分為A一H共8種基因型,其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各不相同。基因型A主要見于北美、北歐、印度及非洲;基因型B和C主要見于亞洲;基因型D主要見于南歐、中東和印度;基因型E主要見于西非和南非;基因型F主要見于南美和中部美洲;基因型G主要見于美國和歐洲。基因型H新近自中部美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患者中分離。HBeAg(-)的HBV(前C變異株)最常見于基因型B、C及D,這可以解釋為何HBV前C變異株感染最常見于亞洲和南歐。
初步資料顯示,HBV基因型可能和臨床后果相關。亞洲一些研究提示,較之基因型B,基因型C與重型肝病及HCC的關系更為密切。與基因型C相比,在較輕的年齡段基因型B似更易發生HBeAg血清學轉換。尚無資料顯示HBV基因型可持續影響口服核苷(酸)類似物的治療效果,但有資料顯示,HBV基因型可影響對干擾素(IFN)的應答,因為基因型A和B與基因型D和C相比看來相對易于獲得較高的對IFNα-2b的抗病毒應答。此外,有報道稱,HBV基因型A在PEG-IFNα-2a治療后有相對較高的HBeAg血清學轉換率;基因型A和B在應用PEG-IFNα-2b治療后有相對較高的HBeAg消失率。
鑒于這些新出現的資料,我們建議應當對患者常規進行HBV基因型檢測,以幫助判斷哪些患者具有疾病進展的高風險,特別是哪些患者最適合應用PEG-IFN治療。對影響抗病毒治療的可能因素或應答方面的認識,促進了對選用PEG-IFN還是口服(核苷類)藥物進行抗病毒治療的廣泛討論。目前,有關參照實驗室已廣泛提供HBV基因型檢測的商業化服務。
五、HBV感染的診斷指標
慢性HBV感染的診斷指標主要包括血清中HBV血清學和病毒學指標的檢測,以及反映肝臟病變狀態的血清生化學和組織學指標的檢測。
(一)血清學指標 HBsAg是HBV感染后首先出現的血清學標志物。若HBsAg在體內持續存在6個月以上,提示存在慢性HBV感染。抗-HBs的出現表示HBV感染恢復和(或)對HBV產生免疫。在接種乙型肝炎疫苗后,也可出現抗-HBs。偶爾,在慢性HBV感染者體內可同時檢測出抗-HBs和HBsAg,但目前對其意義尚不清楚。HBeAg的存在提示HBV復制活躍,但HBeAg消失并不意味病毒復制缺如,因為在HBeAg(-)的HBV感染(前C或C啟動子變異)時并不能測及HBeAg。抗-HBe的存在常提示發生了HBeAg血清學轉換,盡管它也可以出現于前C或C啟動子變異的HBV感染。HBeAg(+)患者的血清學轉換(HBeAg消失并測及抗-HBe)常被看成是抗病毒治療的終點,因為有資料顯示這種情況通常與疾病進展的風險降低相關,但這并不能保護患者以后不發展為HCC。
(二)病毒學指標 血清HBV DNA載量反映了病毒復制的水平。以往采用非擴增性雜交分析法檢測血清HBV DNA,但這種方法敏感性有限,定量檢測的下限高達105一106拷貝/ml,因此不應繼續用于慢性HBV感染者的常規監測管理。美國NIH乙型肝炎管理組推薦,若應用非擴增性雜交分析法能夠測及HBV DNA,亦即HBV DNA>105拷貝/ml(20 000 IU/ml),應當給予抗病毒治療。然而,部分HBeAg(+)及許多HBeAg(一)的患者,其體內的HBV DNA具有波動性,有時可降至105拷貝/ml以下。而且,目前并不清楚與進展性肝病相關的HBV DNA臨界值究竟是多少。根據專家組成員的經驗,即使患者血清HBV DNA水平持續<20 000 IU/ml,也可能存在進展性肝病。因此,HBV DNA低水平的臨床意義并不確定,應當進行個性化分析。
理想的HBV DNA檢測方法應當具有線性大動力學范圍的定量能力,以允許在最低和最高病毒濃度時均能對病毒血癥進行評估。目前,Roche COBAS Taqman HBV DNA分析系統擁有當前所能達到的最低檢測下限和最廣的線性定量范圍(<50一109拷貝/ml)。實時聚合酶鏈式反應(PCR)分析法的應用已越來越廣泛,在對患者進行初始病情評估時應優先選用,特別重要的是對接受和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患者進行監測。目前,在不同的監測方法之間尚缺乏標準化,因而難以對不同實驗室之間的數據進行比較。這一問題有望通過建立一種標準HBV DNA定量檢測法而得以解決。將來,所有的結果都應當以IU/ml為單位進行報告(1 IU/ml約相當于5.6拷貝/ml)。
(三)生化學標志 血清ALT水平升高是存在肝組織壞死性炎癥活動的標志之一。因此,ALT水平正常一般被認為預示著肝損害處于組織學靜止期。ALT水平持續正常的HBV感染者,其肝活檢標本的炎癥情況常較ALT水平升高者為輕。由于ALT水平正常的HBV感染者對抗病毒治療的血清學應答常很弱,因此一般認為不宜給予抗病毒治療。然而,肝活檢顯示一部分ALT水平正常但HBV DNA水平較高的患者確實存在顯著的肝臟炎癥和纖維化。新近的3篇初步報告顯示,12%一43%ALT水平持續正常的慢性HBV感染者存在2期或2期以上肝纖維化。其中2篇報告提示,年齡大于40一45歲是預測顯著肝組織學改變的獨立因素。綜合而言,這些研究提示,對年齡大于40一45歲的ALT水平正常的慢性HBV感染者的處理原則應當包括更積極的肝活檢,因為12%一43%的這類患者存在2期或2期以上肝纖維化。這些患者可能需要抗病毒治療。
在許多研究機構,ALT水平的正常上限值可能被高估,因為ALT正常參考范圍的制訂可能包含了一部分亞臨床肝病患者。有一項大型回顧性研究包含了一組因首次獻血而需要篩查肝病的人群。這項研究所獲得的血清ALT正常上限在男性為30IU/L,女性為19 IU/L,顯著低于先前所建立的標準。而且,一項包括95533例男性和47522例女性(年齡在35一59歲)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顯示,ALT水平按新標準屬于輕度升高但仍在傳統正常參考范圍內的患者,其肝病死亡的相對危險度較高。與ALT水平<20 IU/L的個體相比,ALT水平在20一29 IU/L之間的患者,其病死相對危險度高2.9倍,ALT水平在30一39 IU/L之間的患者,其病死相對危險度高9.5倍。因此,調查小組建議,在決定是否開始抗病毒治療時,將ALT水平的正常上限值男性定為30 IU/L,女性定為19 IU/L。
(四)組織學指標 對肝活檢標本的組織學評估是較血清ALT水平更為敏感和準確的肝病標志。在開始抗病毒治療之前,對肝組織學的基線狀態進行評估,并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病是非常有用的。然而,肝活檢并非能夠經常性使用的診斷手段。由于其帶有侵入性,因此部分患者會拒絕進行肝活檢。近幾年來,肝纖維化非侵入性血清學標志物的研究取得了顯著進展。雖然這些資料令人鼓舞,但這些方法尚未得到全面驗證,因此尚不宜進人臨床常規應用。
六、患者評估

表3總結了慢性HBV感染者在初始評估時應當進行的檢查項目,并建議對不考慮給予抗病毒治療的患者進行隨訪評估。初始評估應當包括全面的病史和體格檢查,特別注意HBV感染和肝癌家族史,與其他病毒同時感染的危險因素以及酒精的飲用等。實驗室檢查項目應當包括:對肝病狀態的評估,HBV復制標志物,HBV基因型;有其他病毒感染風險的患者,也需對同時感染的其他病毒進行檢測。對于ALT持續或間歇升高的患者,推薦進行肝活檢,但不可強制進行。在有HCC高風險的患者,應篩查HCC。應當對患者提出忠告,提醒其注意預防HBV感染的傳播,性伴侶和家庭密切接觸者應進行預防接種。應規勸患者不要過度飲酒,并忠告他們并不存在能夠得到證實的所謂酒精飲用的安全水平。對于有肝硬化的患者,建議禁酒。所有未對甲型肝炎病毒(HAV)產生免疫的慢性HBV感染者,應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建議進行疫苗接種(甲型肝炎疫苗2個劑量,初始注射1次,在6—18個月加強注射1次)。
(一)肝細胞癌的篩查 HBV攜帶者發生HCC的風險增加。在絕大多數患者,HCC最初是以有包膜的單個腫瘤形式出現。其倍增時間從2-12個月不等(平均4個月)。通過定期進行甲胎蛋白(AFP)和超聲波(US)檢查,可以早期發現HCC。分別應用AFT和US對HBV感染者進行定期篩查,在HCC患者中發現小肝癌(<5 cm)的幾率分別約為64%和83%。聯合應用AFP和US進行檢查,優于單獨應用其中任意一種方法。資料顯示,每6個月進行1次AFP和US檢查,較之每年進行1次檢查,能更有效地發現HCC,但每3個月和每6個月檢查1次,在發現HCC的效率方面沒有明顯差異。
篩查HCC的標準方法在AASLD實踐指南和EASL共識指南中均有概要描述,并且新近進行了修訂。應當對有發生HCC高風險的HBV攜帶者進行篩查。這些高風險患者包括超過40歲的亞洲男性患者,超過50歲的亞洲女性患者,超過20歲的非洲患者,肝硬化患者,有HCC家族史的患者,HBV DNA水平較高的患者和(或)有肝臟炎癥活動的患者。對于據推測在出生時或幼兒時期即已感染HBV的亞洲患者,許多臨床醫師推薦在更早期(30一35歲或更年輕)進行HCC篩查。必須清醒認識到的重要情況是,在乙型肝炎患者,HCC可以在無肝硬化的情況下發生。應當每6個月進行1次AFP和US篩查。磁共振成像檢查(MRI)和計算機斷層掃描(CT)價格較貴,但一般認為它們對HCC的診斷敏感性高于US,因此臨床醫師建議對某些患者(例如因肝硬化或肥胖而使US對HCC的診斷敏感性很低時)采用MRI或CT進行篩查。雖然AFP的診斷敏感性很低時)采用MRI或CT進行篩查。雖然AFP的診斷敏感性不如US,但有很高的陰性預測值(99%)。應考慮對HBV感染地方流行區的HCC低危人群進行HCC定期篩查。
七、抗病毒治療對象
雖然對慢性HBV感染者在初始評價時應當進行檢測的指標(見表3)有普遍一致的認識,但對如何應用這些檢測指標來鑒別抗病毒治療患者,某些問題尚存在爭論。
(一)ALT水平正常或升高者 ALT水平是評價肝病狀況的指標之一,對確定哪些患者應作為抗病毒治療對象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將ALT水平升高作為篩選抗病毒治療對象的必備前提條件有其局限性。肝細胞壞死的程度和ALT 水平升高并非總是相關,僅僅檢測ALT可能難以真正篩選出有肝組織壞死性炎癥或肝纖維化的患者,這與丙型肝炎情況相似。此外,ALT的活性可能與體重指數(BMI)、性別、異常的脂質和碳水化合物代謝,以及患者是否接受透析治療等因素獨立相關。再者,ALT升高可出現于多種不同的情況,例如自發性HBeAg消失、某些抗病毒治療或有其他病毒感染時。
ALT水平對抗病毒決策有重要影響,因為其可用來預測對拉米夫定、IFN, PEG-IFNα-2a及阿德福韋的血清學應答(HBeAg消失或血清學轉換)。ALT水平對抗病毒治療應答的預測價值可從下述現象中進一步得到證實:雖然亞洲患者對抗病毒治療的應答普遍較低,但ALT水平升高的患者對拉米夫定和IFN的應答狀況與同等病情的高加索人種相似。
不同的地理起源及HBV基因型也影響ALT作為抗病毒決策因素的效用性。絕大多數亞洲患者ALT水平正常,但至少1/3的患者罹患CHB。在早年即獲得HBV感染的亞洲和其他地區的患者,常在HBV感染的免疫耐受階段獲得診斷,此階段的特征是肝組織缺乏壞死性炎癥活動,ALT水平正常,但HBV復制活躍。在亞洲和其他地區患者中發現的HBV基因型B和C易發展為HBeAg(-)的變異株(前C和C啟動子變異株)。這些患者盡管存在抗-HBe,甚至ALT水平也正常,但體內HBV復制活躍。
以ALT水平來確定需要抗病毒治療的對象,這種做法來自應用IFN治療的歷史經驗有助于篩選出更能對抗病毒干預產生應答的患者群體,但ALT水平本身并非所謂需要有效治療的疾病狀態。根據HBV感染的自然史,抗病毒治療原則應當對需要進行抗病毒治療患者的疾病狀態作出界定,然后才能進行抗病毒治療選擇。雖然了解患者的ALT水平有助于對病情作出判斷,但正常的ALT水平并不總是能幫助決定哪些患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的ALT水平需要與血清HBV DNA及年齡等因素結合起來進行考慮。因此,對于HBV DNA≥104IU/ml且ALT正常的患者應考慮進行肝活檢,尤其是那些年齡大于35-40歲、估計不太可能處于免疫耐受狀態的患者。若肝活檢發現存在顯著的肝臟損害,亦即中度(2期)或中度以上肝纖維化和(或)顯著的壞死性炎癥的患者,應當接受抗病毒治療。對于HBV DNA≥104IU/ml且ALT水平升高的患者,不論是否進行肝活檢,一般應給予抗病毒治療。
(二)病毒(HBV DNA)閾值 傳統上,以雜交技術檢測HBV DNA的結果為“陽性(超過檢測下限)”或“陰性(低于檢測下限)”是判斷抗病毒治療對象的主要決定因素。這是因為在大多數已經發生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其HBV DNA水平降至非擴增性測定法的檢測下限(<105拷貝/ml),ALT水平恢復正常,壞死性炎癥減輕。CHB患者的HBV DNA水平具有波動性,有時可能會低于這種檢測下限。此外,與肝病進展相關的HBV DNA閾值目前并不清楚。以往認為,用雜交技術不能測及的HBV DNA水平在臨床上沒有顯著性意義,而低于20 000 IU/ml的血清HBV DNA水平與肝內顯著的HBV DNA及共價閉合環狀DNA(cccDNA)水平是相關的。再者,對于應用雜交法不能測及肝硬化和HCC患者的HBV DNA(其HBsAg檢測結果也為陰性),現應用PCR法已在其血清及肝臟中測出HBV DNA。敏感的實時靶向擴增試驗,例如Roche Taqman PCR分析法,可檢測到低至10 IU/ml(50拷貝/ml)的HBV DNA水平。雖然低水平HBV DNA的臨床意義尚不清楚,但有資料顯示HBV DNA<105拷貝/ml的患者有發展為肝硬化和HCC的危險。
隨著敏感的實時PCR分析法的出現,血清HBV DNA水平在對CHB患者的隨訪評估中已成為最為有用的衡量手段。對26份前瞻性研究報告的回顧分析發現,病毒載量水平或病毒載量的變化與多種被廣泛接受的疾病活動標志(組織學分級、生化學和血清學應答)顯著相關。為了確定是否存在一個具有顯著性臨床意義的HBV DNA閾值,Chu等采用PCR法對處于不同疾病階段的165例中國患者序貫樣本的HBV DNA進行了分析。在自發性或IFN治療后發生HBeAg清除的患者,血清HBV DNA載量平均下降了3 log10,但并沒有某一種HBV DNA閾值與HBeAg的消失相關。而且,HBeAg消失時的血清HBV DNA載量并不能作為HBeAg消失持久性的預測指標。HBeAg(+)患者較HBeAg(-)患者傾向于擁有較高水平的HBV DNA (105一108拷貝/ml),但在某些HBeAg(-)患者也測及了高達108拷貝/ml的HBV DNA。再者,大約1/3的HBeAg(-)患者的HBV DNA水平持續超過105拷貝/ml有意思的是,2/3的HBeAg(-)患者和幾乎所有的非活動性攜帶者的HBV DNA水平均持續小于105拷貝/ml,提示不可能確定一個HBV DNA臨界值(cut-off value)來區分非活動性攜帶者和HBeAg(-)的CHB患者。反復測定HBV DNA和ALT水平或肝活檢結果有助于對這些患者進行區分,雖然肝活檢并不常用。在另一項研究中,Manesis等報道,以敏感的定量PCR法測得的病毒載量30000拷貝/ml是區分HBeAg(-)CHB和非活動性HBsAg攜帶狀態的合適HBV DNA水平。鑒于HBeAg(-)CHB的HBV DNA水平具有波動性,他們還建議對ALT水平正常及血清HBV DNA低水平的患者在多個時間點進行動態監測,以區分究竟屬于非活動性攜帶者還是HBeAg(-)CHB。
最理想的CHB處理策略需使用敏感的實時PCR法建立準確的基線HBV DNA水平,然后在抗病毒治療過程中繼續應用敏感的方法監測最準確的治療應答以及與耐藥相關的病毒學反彈(rebound)。應用非PCR法有可能檢測不出顯著的病毒復制,以及具有潛在有害的臨床后果,不論是在治療前還是治療中。
(三)患者種群 在亞洲絕大多數慢性HBV感染來自圍產期傳播。這些患者HBeAg持續存在的時間較長(免疫耐受階段),ALT水平多傾向于正常,血清HBV DNA水平可以很高。絕大多數這類患者直到30或40年后才發生HBeAg清除或血清學轉換,而繼續呈現HBeAg(+)的患者,要么依然處于免疫耐受狀態,要么在以后發展為下述的西方發達國家模式(Western pattern of hepatitis)并出現ALT水平的持續或間歇性升高。即使是出現HBeAg清除的患者,也具有發展為HBeAg(-)CHB的高度風
險,后者病情嚴重。
亞洲患者傾向于在感染HBV的60一70年后,發生CHB的重要并發癥——HCC,且常常在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之后。雖然ALT升高的亞洲患者對IFN及拉米夫定的應答狀況與高加索人種相似,但當前許多亞洲患者的ALT水平正常,因此對抗病毒治療的應答率較低。在亞洲患者,IFN極少能持久清除體內的HBV。新近對一組中國患者在IFN治療后的隨訪研究顯示,即使是在HBeAg血清學轉換之后,應用PCR法仍能在91%的患者體內檢測出HBV DNA。而且,這些患者肝硬化及HCC的發病率依然很高。相比之下,在高加索人種,IFN在清除HBeAg后還可增加HBsAg的清除,因而有較好的臨床和存活結果。
乙型肝炎的第二種血清學模式見于非洲、地中海國家及美國阿拉斯加州。這些地區的HBV傳播模式趨向為兒童期的“人一人”傳播。許多HBeAg(+)的兒童伴有ALT升高,HBeAg的血清學轉換趨向于在大齡兒童或十幾歲時發生。這類人群的HBV感染自然史介于亞洲人群和西方人群之間。乙型肝炎的第三種模式見于西方發達國家,也明顯不同于亞洲人群中的模式。HBV感染在成人期獲得,經由性暴露、靜脈內注射毒品或輸血傳播。其HBV感染的慢性化風險在這第三類群體中是最低的,小于5%。西方國家的CHB患者趨向表現為ALT和HBV DNA水平較高,在總體上對抗病毒治療的應答較好。
八、治療目標
CHB治療的目標是清除或顯著抑制HBV復制,防止肝病進展為肝硬化,因為肝硬化可導致肝功能衰竭和HCC,并最終引起患者死亡或需要進行肝移植。因此,治療的首要目標是降低或維持HBV DNA在最低水平(即持續抑制HBV DNA復制)。而這又引發其他治療目標,包括肝組織學的改善和ALT的正常化。在治療前HBeAg(+)患者尚有另外一個治療目標,即HBeAg消失伴血清學轉換為抗-HBe,后者是治療所希望的,因為完全的HBeAg血清學轉換提示可以停止抗病毒治療,而且在停藥后繼續維持療效的可能性很大。雖然HBsAg消失是十分理想的目標,但短期的抗病毒治療很難達到這種效果,因此并不作為常用的抗病毒指標。
九、已批準用于治療HBV感染的藥物
從1992一2005年,美國批準用于治療慢性HBV感染的藥物包括:IFNα-2b、拉米夫定、阿德福韋、恩替卡韋及PEG- IFNα-2 a。IFNα-2b的治療應用已被PEG-IFNα-2a取代,因此本治療推薦意見中不再包含這種選擇。目前數種新的抗病毒藥物和免疫調節治療正處于考察中,但尚未進人臨床商業化應用,亦不加以討論。
十、CHB的治療和管理
(一)HBeAg(+)患者 阿德福韋、恩替卡韋、IFNα-2b、拉米夫定及PEG -IFNα-2a被批準用于HBeAg(+)的慢性HBV感染者的一線抗病毒治療。
1.主要臨床資料概述
(1)阿德福韋醋 服用阿德福韋10 mg,口服,每日1次,連續1年,肝組織學獲得改善,血清HBV DNA和ALT水平下降,HBeAg血清學轉換率增加(見表4)。治療超過48周的患者獲得了進一步的病毒學、血清學和臨床效益。在服藥第144周,53%的患者出現HBeAg消失,46%的患者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48%的患者不能測及HBV DNA,80%的ALT正常。新近,對HBeAg(-)患者的隨機、對照、前瞻性隊列研究的一項開放標記(open-label)延伸試驗的初步報告顯示,長期應用阿德福韋治療4—5年可使肝纖維化持續改善。在治療4年和5年后,ALT水平正常者分別為70%和69%,HBV DNA水平小于3log10拷貝者分別為65%和67%。6例(5%)患者HBsAg消失,其中5例患者出現抗-HBs。這些患者也出現持續的肝組織學改善。阿德福韋的安全性與安慰劑相似。在10mg治療組,沒有患者出現血清肌升高≥0.5mg/dl,盡管肌升高可見于較高劑量的阿德福韋治療(在30mg治療組有8%的患者出現血清肌的升高)。雖然尚缺乏1年以上的比較資料,但血清肌水平異常的發生率在第1年無明顯差別。腎毒性僅見于藥物早期研發階段使用較高劑量的阿德福韋時。與拉米夫定相比,阿德福韋在治療1年時未發現耐藥相關變異。新近的4—5年隨訪研究的耐藥監測資料顯示,阿德福韋治療在第2、3、4和5年出現耐藥變異(N236T和A181V/T的患者百分率分別為3%、11%、18%和29%。阿德福韋治療48周后出現HBV DNA水平升高的患者,發生耐藥的風險最高。體外試驗顯示,N236T變異對拉米夫定和恩體卡韋仍然敏感。然而,A181V變異對拉米夫定和恩替卡韋的敏感性下降,但對替諾福韋(tenofovir)仍敏感。研究顯示,伴有血清HBV DNA和ALT水平反彈的阿德福韋耐藥對拉米夫定治療仍可產生應答。至于阿德福韋耐藥對其他臨床終點的影響,目前尚缺乏足夠的資料。
(2)恩替卡韋 與服用拉米夫定100mg/d相比,恩替卡韋為0.5mg/d,48周時所獲得的組織學改善率更高(72%對62%),HBV DNA下降程度更強(-6.9對-5.4log10),HBV DNA<300拷貝/ml的患者更多(67%對36%),ALT≤1×ULN者更常見(68%對60%)。雖然恩替卡韋是目前降低血清HBV DNA效果最強大的口服藥,但治療1年的資料顯示,其對HBeAg消失或血清學轉換的影響與拉米夫定相比差異無顯著性(見表4)。恩替卡韋服用48周以上的安全性特點與拉米夫定相似。
新近一項初步報道表明,對治療48周后僅獲得病毒學應答,即僅出現HBV DNA<0.7Meq/ml但HBeAg仍陽性的患者,繼續給予恩替卡韋或拉米夫定治療。2年后,不能測及血清HBV DNA的患者比例恩替卡韋組顯著高于拉米夫定組(80%對39%,P<0.0001),恩替卡韋組的HBeAg血清學轉換率似乎也高于拉米夫定組(31%對25%,但差異無顯著性)。不論是治療48周還是96周,恩替卡韋組均未發現HBV DNA聚合酶變異。恩替卡韋的高效應率和治療2年仍無耐藥變異,成為CHB抗病毒治療的一個極佳選擇。
(3)干擾素 對15項試驗的薈萃分析顯示,IFN治療可促進HBeAg消失和HBeAg血清學轉換(見表4)。ALT水平升高和低水平血清HBV DNA是對干擾素治療產生應答的最好預測指標。許多亞洲慢性HBV感染者ALT正常,甚至在高水平HBV DNA時也是如此,因此對IFN的應答很差。在歐洲的研究中觀察到開始IFN治療的1年內有5%一10%的患者HBsAg消失;在產生持續應答的患者中,這一比例在第5年升至11%—25%。但在亞洲患者中未能觀察到這種研究結果。IFN需要皮下注射,在治療過程中可出現多種不良反應,例如流感樣癥狀、疲勞、厭食、抑郁及白細胞減少等。對于選擇以IFN為基礎的治療方案的患者,PEG-IFN將有可能取代標準IFN的使用。
(4)拉米夫定 應用拉米夫定治療1年可獲得組織學改善、HBeAg血清學轉換、HBV DNA抑制及ALT復常(見表4)。如果在HBeAg血清學轉換之前即停止治療,將重新出現病毒復制。因此,許多患者需要進行長期治療。HBeAg的血清學轉換率隨拉米夫定應用時間的延長而提高,從治療1年時的17%升高至第2、3、4、5年時的27%、40%、47%、50%。HBeAg的血清學轉換率還隨治療前ALT水平的升高而升高。對4項拉米夫定試驗的分析顯示,治療前ALT>5×ULN的56%患者出現HBeAg消失。不幸的是,拉米夫定的耐藥率隨治療時間的延長而增加,由第1年時的14%升高至第5年時的69%。發生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其HBV DNA和ALT水平趨于向治療前的水平反彈。最近的資料顯示,某些患者的初步肝組織學改善可出現逆轉。而且,在某些患者,拉米夫定耐藥毒株的出現與嚴重的ALT
反跳(flares)甚至與迅速的肝功能失代償相關。患者對拉米夫定的耐受性良好,安全性也極佳。
(5)PEG-IFNα-2a 不論是否與拉米夫定合用,應用PEG-IFNα-2a治療48周所獲得的HBeAg血清學轉換率、HBV DNA陰轉率及ALT的復常率均顯著高于單獨應用拉米夫定治療時(見表4)。治療后24周時的HBeAg血清學轉換率,在單獨應用PEG-IFNα-2a組、PEG- IFNα-2a和拉米夫定聯合治療組及單獨應用拉米夫定組分別為32%、27%和19%。雖然PEG-IFNα-2a和拉米夫定聯合治療能獲得更顯著的病毒載量下降,但對于HBeAg的血清學轉換率而言,聯合治療似乎并不比單獨應用PEG-IFNα-2a優越。較高的HBeAg血清學轉換率見于HBV基因等情況下。雖然報道PEG-IFNα-2a的不良反應明顯多于拉米夫定,但其安全性明顯好于普通干擾素。
(6)聯合治療 一些試驗提示,拉米夫定和IFN聯合治療可獲得某些相加效果,但尚需良好設計的大樣本研究來證實這些初步觀察結果。新近在HBeAg(-)和HBeAg(+)患者中進行的研究顯示,聯合應用PEG-IFNα-2a和拉米夫定,與單獨應用PEG-IFNα-2a治療1年后比較,無相加作用。一項小型雙盲單中心研究表明,30例患者隨機接受阿德福韋或阿德福韋加恩曲他濱治療,48周后聯合治療組HBV DNA的抑制程度顯著高于阿德福韋單獨治療組(5. 44 log10對3.40拷貝/ml)。然而,在另一項相似的研究中,應用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韋聯合治療并不比單獨應用拉米夫定療效好。聯合治療在預防耐藥方面可能更有效,但尚需良好設計的大樣本臨床試驗來證實。
(7)應答的持久性 4一8年的隨訪評估顯示,80%一90%的患者在IFN治療后可誘導持久的HBeAg消失。有關拉米夫定治療后應答持久性的資料有限。一項對拉米夫定治療期間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患者的隨訪研究顯示,平均隨訪37個月(5一46個月)后,仍能保持血清學轉換的患者為77%(30/39)。絕大多數臨床醫師認為,HBeAg的血清學轉換優于單純的HBeAg消失,但目前仍不能確定對拉米夫定治療應答的持久性是否受這種差別的影響。拉米夫定誘導的HBeAg血清學轉換的持久性可能受到HBeAg血清學轉換后繼續治療期限的影響。在韓國的一項研究中,HBeAg血清學轉換后繼續服用拉米夫定至少4個月的患者,較之僅繼續服用2個月的患者,其2年復發率較低(32%對74%)。這些資料支持在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后繼續服用拉米夫定至少6個月。新近一項對61例血清HBeAg和HBV DNA(溶液雜交法)持續陰性的患者至少應用拉米夫定治療24個月,撤除拉米夫定治療后血清HBV DNA的累積復現率在6個月、1年和2年時分別為15%、21%和31%,血清HBeAg的累積復現率分別為11%,13%和16%,提示拉米夫定的長期追加治療可增加HBeAg血清學轉換的持久性。
對一組阿德福韋治療結束的患者平均隨訪觀察55周,顯示阿德福韋治療后獲得持久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為91%。持久保持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較未能持久保持HBeAg血清學轉換者的轉換后繼續治療時間為長(48周對23周)。恩替卡韋治療結束后第24周,持久保持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為82%。總之,在結束抗病毒治療后隨訪6個月時,持久保持HBeAg血清學轉換的患者在INFα-2b為80%一90%,在拉米夫定為50%一80%,在阿德福韋為91%,在恩替卡韋為82%。
(8)治療應答的預測指標 一系列臨床、生化和血清學指標被用作判斷對IFN有良好應答的預測指標。然而,最好的預測指標是ALT和HBV DNA水平。這些參數還與較高的自發性HBeAg血清學轉換率相關。新近的研究顯示,HBV基因型可能影響對IFN的應答。治療前ALT水平較高也是預測對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韋治療有良好應答的最好指標。
2.治療建議:HBeAg(+)患者
對HBeAg(+)患者的治療推薦意見總結于表5。專家小組推薦將血清HBV DNA≥20 000 IU/ml作為HBeAg(+)患者合理的治療閾值。對HBV DNA<20 000 IU/ml的患者,不推薦常規進行抗病毒治療,因為大多數這類患者屬于非活動性HBsAg 攜帶者,肝病發作的風險較低。由于存在疾病的生化學、組織學及臨床進展的風險,因此應當以敏感的HBV DNA檢測方法進行積極的監控。以逐例患者的具體情況為基礎,必要時可進行肝活檢,并在發現有顯著的肝病組織學證據時考慮給予治療。對不治療的患者應在初期1年每3個月監測1次,以保證HBV DNA和ALT水平確實處于穩定狀態;若經監測后仍然穩定,則在以后每6-12個月監測1次。
a.數量單位為IU/ml(1 IU/ml約等于5 .6拷貝/ml)
b.血清ALT濃度的正常上限定為男性30 IU/L,女性19 IU/L
c.在初期診斷,1年中每3個月檢查1次,以確保穩定性
d.檢測HBV基因型可能有助于決定是使用PEG-IFNα-2a還是阿德
福韋或恩替卡韋(PEG-IFN對HBV基因型A的治療效應優于基
因型D)
e.優先選擇PEG-IFNα-2a和恩替卡韋而不是拉米夫定,因為隨機臨
床試驗顯示前兩者療效相對較好,而拉米夫定的應用還受到高
耐藥率的限制
對血清HBV DNA≥20 000 IU/ml的HBeAg(+)患者,應根據ALT水平決定是否給予治療。ALT水平正常和ALT水平升高的患者出現病毒抑制的幾率接近,但前者出現HBeAg消失的幾率較低。由于ALT水平正常的患者也可以存在顯著的肝組織學病變,且病毒抑制與組織學應答相關,因此應考慮對這些患者進行肝活檢,尤其是對年齡超過35-40歲的患者。若肝活檢證實存在肝病,則應當給予治療。對血清HBV DNA≥20 000 IU/ml、ALT正常的患者,其抗病毒治療效果尚需進一步研究。對血清HBV DNA<20 000 IU/ml、ALT升高的患者,拉米夫定、阿德福韋、恩替卡韋或PEG-IFNα-2a均可考慮作為一線選擇藥物。然而,對于血清HBV DNA水平較高和(或)ALT水平正常的患者,阿德福韋或恩替卡韋應作為優先選擇,因為這類患者對IFN治療的應答率低,而拉米夫定耐藥率又較高。測定HBV基因型有助于決定是否采用PEG-IFNα-2a進行治療,因為有資料顯示,感染HBV基因型A的患者對這種抗病毒治療的應答效應在各種基因型HBV感染中是最好的。由于在隨機臨床試驗中已經證實PEG-IFNα-2a和恩替卡韋優于拉米夫定,且拉米夫定有著較高的耐藥率,因此不推薦拉米夫定作為作為HBeAg(+)患者的一線用藥。在ALT水平正常的患者,雖然口服核苷/核苷酸類似物可有效抑制血清HBV DNA,從而具有一定的治療效果,但這種情況下的HBeAg血清學轉換并不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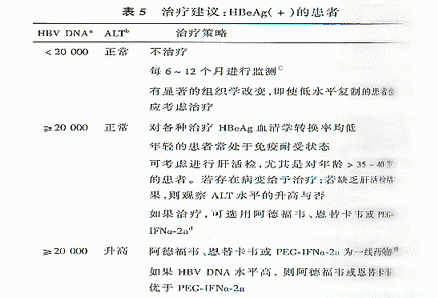
不論是應用恩替卡韋還是阿德福韋治療,在治療期間應當至少每6個月監測1次。若應用拉米夫定治療,為盡早發現耐藥,應進行更密切的監測。根據目前可供參考的資料,專家小組建議對患者應當治療至HBeAg血清學轉換后及HBV DNA水平將至用PCR測不到,然后再繼續治療6一12個月。對于獲得HBeAg血清學轉換但仍能穩定測得HBV DNA的患者,應繼續治療6個月;在再次證實HBeAg的血清學轉換后,可考慮停藥(對非肝硬化患者)。對復發的患者可進行再治。HBeAg(+)患者若未能獲得HBeAg消失,則應長期治療,因為HBeAg的血清學轉換隨時間延長而增加。
(二)HBeAg(-)患者 HBeAg(-)慢性HBV感染者的治療終點較HBeAg(+)患者更難進行評估,因為無法運用HBeAg血清學轉換這一衡量指標。因此,HBV DNA的抑制和ALT水平的復常是臨床上唯一實用的判斷治療應答的指標,并且更常需要進行長期治療以維持這些應答。
1.主要資料概述
(1)阿德福韋酯 阿德福韋治療1年,64%的患者可獲得組織學改善,血清HBV DNA水平平均下降3.91log10拷貝/ml(安慰劑組為33%,僅下降1.35 log10拷貝/ml),51%的患者出現血清HBV DNA<400拷貝/ml(安慰劑組無1例出現),72%的患者出現ALT正常(安慰劑組僅為29%)。新近的資料顯示,阿德福韋治療144周可獲得長期病毒學和生化學改善。在第144周,79%的患者血清HBV DNA<1000拷貝/ml,69%的患者ALT恢復正常。一小部分患者在第144周時同意接受附加肝活檢,結果顯示有進一步的肝組織學改善。此外,4年和5年的資料也顯示有持續的肝組織學改善。患者對阿德福韋的耐受性良好,阿德福韋的安全性與安慰劑相似。4例患者(3%)被證實存在血清肌酐升高≥0.5mg/dL。治療滿48周時未觀察到阿德福韋耐藥變異。但隨后觀察到阿德福韋耐藥變異N236T。
(2)恩替卡韋 以恩替卡韋治療48周,與拉米夫定相比,獲得了更為顯著的組織學改善率(70%對61%)、HBV DNA下降幅度(-5.0對一4. 5 log10)及HBV DNA < 300拷貝/ml的患者數(90%對72%)。治療后不能檢測到HBV DNA的患者比例很高,顯示了恩替卡韋強大的抑制病毒的能力。恩替卡韋治療組ALT復常(<1×ULN)率顯著高子拉米夫定對照組(78%對71%),但在肝纖維化的改善方面兩者差異無顯著性。恩替卡韋治療48周以上的安全性特點與拉米夫定相似。在第48周和96周均未發現HBV DNA聚合酶中發生恩替卡韋耐藥變異。
(3)普通干擾素 IFN治療HBeAg(一)患者結束時的應答從40%一90%不等,但復發率卻高達30%一90%。總體上,持續病毒學應答率約為15%一25%。治療12個月的患者應答看起來更持久,而且32%獲得持久病毒學應答的患者可繼續發生HBsAg的清除。接受IFN治療并獲得持久病毒學應答的患者,其生存和無并發癥情況均顯著好于無應答者或未治療者。
(4)拉米夫定 總體上,拉米夫定治療6-12個月后大約2/3的患者可出現生化學和病毒學應答,肝組織壞死性炎癥的改善率也大致如此。但是,一旦停止治療,絕大多數患者會復發,且大多數患者是由于發生拉米夫定耐藥而復發。然而,新近一項研究提示,血清HBV DNA持續不能檢出的患者,2年后可停用拉米夫定,且復發率低于以往的研究報道,但這些結果尚需進一步證實。拉米夫定長期治療可維持正常的ALT水平和檢測不到HBV DNA,但在發生對拉米夫定耐藥的YMDD變異后,可發生生化學和病毒學的反彈。一項長期拉米夫定治療研究顯示,雖然治療12個月時ALT和HBV DNA的應答率分別為96%和68%,但此后應答率隨治療時間的延長而逐步下降。治療30個月以上時,僅約40%的患者維持正常的ALT水平和不能檢測到HBV DNA。拉米夫定耐藥的發生率隨用藥時間的延長而增加,第1年發生YMDD變異的患者為19%一27%,第2年升至44%,第4年高達60%。這類出現YMDD變異株的人群,在臨床上可出現顯著的肝炎,因而顯著限制了拉米夫定對HBeAg(一)慢性HBV感染者的治療作用。
(5)PEG-IFNα-2a 應用PEG IFNα-2a治療48周,與或不與拉米夫定合用,在治療結束后24周顯示了更顯著的ALT復常率,更多患者血清檢測不出HBV DNA(<400拷貝/ml).停藥后24周時,在 PEG-IFNα-2a單獨治療組,ALT復常和檢測不出HBV DNA的比例分別為59%和19%;在PEG-IFNα-2a/拉米夫定聯合治療組,分別為60%和20%;在拉米夫定單獨治療組,分別為44%和7%。PEG-IFNα-2a/拉米夫定的聯合用藥未能顯示比單獨應用PEG-IFNα-2a更好的優勢。HBsAg的血清學轉換率在單獨應用PEG-IFNα-2a組、PEG- IFNa-2a/拉米夫定聯合治療組和單獨應用拉米夫定組分別為3%、2%和0%。拉米夫定耐藥株出現的幾率,聯合治療組明顯低于拉米夫定單獨治療組。盡管報道PEG-IFNα-2a治療組的不良反應明顯多于拉米夫定治療組,但其安全性特點較之常規IFN是令人滿意的。
2.治療建議:HBeAg(-)患者
對HBeAg(一)患者的治療推薦見表6。Chu等報道,在就診時的初期檢測中,大約1/2的HBeAg(一)患者的HBV DNA水平持續低于105拷貝/ml。由于HBeAg(一)患者的血清HBV DNA水平趨于較HBeAg(+)患者為低,但仍可存在肝病,因此專家組建議對HBV DNA ≥ 2 000 IU/ml的HBeAg(一)患者進行治療,而其他建議與對HBeAg(+)患者的推薦意見相似。阿德福韋、恩替卡韋和PEG-IFNα-2a均可作為一線選擇。由于絕大多數患者需要長期治療(除非發生HBsAg血清學轉換,而這一般不可能),因此不推薦使用拉米夫定,因為拉米夫定的耐藥風險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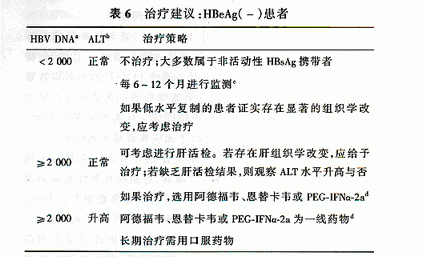
a.數量單位為IU/ml(1 IU/ml約等于5.6拷貝/ml)
b.血清ALT濃度的正常上限定為男性30 IU/L,女性19 IU/L
c.在初期診斷,1年中每3個月檢查1次,以確保穩定性
d.檢測HBV基因型可能有助于決定是使用PEG-IFNα-2a還是阿德
福韋或恩替卡韋(PEG-IFN對HBV基因型A的治療效應優于基
因型D)
e.拉米夫定不被認為是合理的治療選擇,因為長期應用拉米夫定
發生耐藥的風險很高,而且隨機臨床試驗顯示其不如PEG-IFNα-
2a和恩替卡韋
對接受治療的患者應當每6個月監測1次。雖然長期治療(12個月)較短期治療(4一6個月)對停藥后的持續病毒學應答更有利,但對IFN的療程目前仍不十分清楚。專家組相信PEG-IFNα-2a將取代標準IFNα-2b。與口服藥物相比,患者對IFN的耐受性問題比較突出。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需要長期服用,但目前尚缺乏恩替卡韋服藥2年以上的長期資料。治療期間應當每6個月監測1次HBV DNA(PCR法)和ALT水平。
(三)抗病毒治療耐藥的患者 近年來隨著CHB口服抗病毒治療藥物的應用常有相關的耐藥HBV變異株出現。口服抗病毒藥物的耐藥率總結見表7,抗病毒耐藥的命名、預防策略及可能的處理總結見表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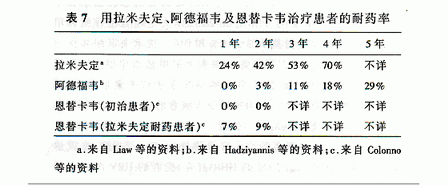
耐藥的發生與初始應答的消失有關,表現為HBV DNA反彈,隨之ALT水平升高,所獲得的組織學改善隨之也發生逆轉;在某些患者,還可出現與病情急性加劇(exacerbations)相關的進展性肝病。拉米夫定耐藥已在所有患者種群中得到描述,包括代償性和失代償性肝病患者、器官移植受者以及存在HBV/HIV合并感染的患者。肝硬化患者耐藥的發生與ALT水平的升高(可能很嚴重)及肝臟合成功能的減退有關,從而導致失代償性肝病。拉米夫定耐藥的預測指標包括:治療前HBV DNA水平較高、非亞洲人種、男性患者和高BMI。在開始治療后獲得HBV DNA水平升高,據此在臨床上可準確診斷出拉米夫定耐藥。這種HBV DNA水平的典型升高與肝臟損害相關(血清ALT水平升高)。這種臨床耐藥診斷與HBV聚合酶變異的基因型標志密切相關,沒有必要通過HBV DNA直接測序來證實耐藥的發生。
在阿德福韋治療48周以上的HBeAg(+)和HBeAg(-)患者中均觀察到對阿德福韋的耐藥變異。一些資料提示,聯合應用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韋進行治療的患者不出現阿德福韋相關的耐藥變異,拉米夫定的耐藥發生率也較低。在未使用過核苷類似物進行治療的患者,應用恩替卡韋治療96周未發現耐藥。但在已經存在YMDD變異引起對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可以觀察到對恩替卡韋的耐藥(見表7)。
1.主要臨床資料概述:對拉米夫定耐藥的HBV
(1)阿德福韋酯 有數項研究對阿德福韋治療拉米夫定耐藥HBV的效果進行了評價。一項研究評價了單用阿德福韋對代償性拉米夫定耐藥HBV的獨立治療效果。與繼續使用拉米夫定不能降低HBV DNA水平相比,單用阿德福韋或阿德福韋/拉米夫定聯合使用均能抑制血清HBV DNA且程度相近。在從拉米夫定轉換到單用阿德福韋治療期間,沒有患者出現臨床上顯著的ALT水平升高。聯合治療時患者的耐受性良好。新近兩項研究提示,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在從拉米夫定轉換為阿德福韋治療后,出現阿德福韋耐藥變異的幾率高于初始抗病毒治療即使用阿德福韋的患者(治療2年時的耐藥變異率分別為15%和19%對3%)。新近另一項研究顯示,先前接受或未接受過拉米夫定治療的患者,阿德福韋和拉米夫定的聯合使用要比單用阿德福韋治療可獲得更強和更持久的HBV DNA水平的抑制(6.2log10對4.2log10),但低于HBV DNA檢測線患者的比例在兩組之間相近,生化學和組織學應答也相近。這些研究顯示,應當考慮聯合治療預防以后發生病毒耐藥。在轉換為接受阿德福韋治療的進展性肝病患者,考慮到與阿德福韋耐藥相關的臨床后果,在肝硬化患者中繼續使用拉米夫定加阿德福韋的可能更慎重些。
(2)恩替卡韋 一項研究對HBeAg(+)的拉米夫定耐藥患者應用較高劑量的恩替卡韋(1.0mg/d)進行治療,并與持續應用拉米夫定100mg/d進行對照。結果顯示,恩替卡韋組獲得的組織學改善率(55%對28%),HBV DNA降低的幅度(-5.14對-0.48log10),HBV DNA<400拷貝/ml的患者比例(21%對1%),HBeAg的消失率(10%對3%)和ALT<1.25×ULN的復常率(75%對23%)均優于對照組。然而,上述各個指標的終點應答與初始抗病毒治療即直接使用恩替卡韋的患者相比均較低。此外,拉米夫定耐藥患者治療1年后,7%的患者出現新的耐藥變異,1.6%的患者出現了反彈,血清HBV DNA水平升高。2年的隨訪評估顯示,9%的患者出現耐藥并發生病毒學反彈(見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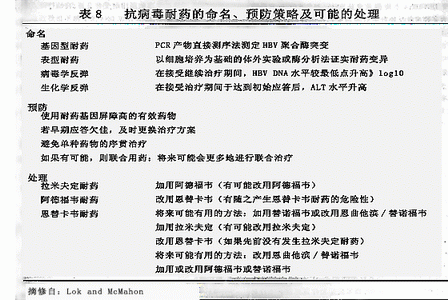
2.治療建議:對拉米夫定耐藥的HBV患者
發生HBV耐藥后患者的處理選擇總結見表8。對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阿德福韋和恩替卡韋均是可以接受的選擇。然而,根據目前的資料,在處理拉米夫定耐藥的HBV,阿德福韋可能優于恩替卡韋。究竟是采用阿德福韋單獨治療,還是阿德福韋與拉米夫定聯合治療,取決于患者的肝病狀態。失代償性肝病患者的資料顯示,若從拉米夫定轉換為阿德福韋治療,某些患者可出現ALT水平輕度升高,但并無患者出現臨床上顯著的ALT升高。這些觀察結果提示,許多患者從拉米夫定轉換為阿德福韋治療是一個安全的策略。在罹患進展性肝病的患者,若HBV變異株回復為HBV野生株,則具有潛在的更為嚴重的災難性后果;若轉換為阿德福韋治療,則在2年后對阿德福韋的耐藥率高達15%一19%。因此,對于拉米夫定耐藥的肝硬化患者,宜在繼續使用拉米夫定的基礎上加用阿德福韋進行治療。關于進行中的研究,其資料將在以后揭曉。對于所有拉米夫定耐藥患者,在繼續使用拉米夫定的基礎上加用阿德福韋,可能優于轉換為阿德福韋單獨治療。恩替卡韋可使拉米夫定耐藥患者的血清HBV DNA水平下降5 log10,但這種治療效應需結合恩替卡韋新的基因變異進行權衡,因為對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在改用恩替卡韋治療1年和2年時的耐藥率分別為7%和9%。未來治療拉米夫定耐藥的措施包括:加用替諾福韋,或改用恩曲他濱/替諾福韋聯合治療。推薦的阿德福韋療程及對治療的監測,需結合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考慮。一般地,對代償性HBeAg(+)患者應治療至HBeAg血清學轉換及不能檢測出HBV DNA (PCR法),然后再繼續追加治療6個月(參見“治療建議:HBeAg(+)的患者”)。
3.主要臨床資料概述:對阿德福韋耐藥的HBV
目前尚無評價阿德福韋耐藥治療的正式研究。來自個案研究的臨床資料顯示,對出現阿德福韋耐藥相關突變N236T或A181V/T的患者應用拉米夫定治療,可獲得病毒學應答。另一個可能的策略是轉換為恩替卡韋治療,前提是此前未出現過拉米夫定耐藥。未來可能的治療選擇是改用恩曲他濱/替諾福韋聯合治療(見表8)。
(四)肝硬化患者(包括終末期肝病患者)
在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手段出現之前,代償性肝硬化和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別為84%和14%一35%。各種臨床參數,如血清膽紅素水平及年齡較大等可預測生存率。此外,在代償性肝硬化HBeAg消失患者的5年生存率為97%,而HBeAg(+)的患者為72%,提示病毒復制可導致不良后果。
1.主要臨床資料概述
(1)阿德福韋酯 一項“姑息治療研究( compassionate-use
study)”應用阿德福韋10 mg/d治療CHB伴代償或失代償性肝硬化,有拉米夫定臨床耐藥證據和進人等候肝移植(226 例)或肝移植后(241例)的患者。肝移植后患者的在阿德福韋治療144周后,血清HBV DNA<1 000拷貝/ml者為78%,ALT水平正常者為58%。肝移植前患者的隨訪評估時間較短,在治療96周后,血清HBV DNA不能測及者占76%,ALT水平正常者占84%。大多數患者反映肝臟合成功能的指標得到改善,Child-Turcotte- Pugh評分保持穩定或有改善。肝移植前患者和肝移植后患者在治療2年后的生存率分別超過80%和90%。在這些患者群中,阿德福韋的安全性特點與患者肝病的階段和并存病一致。血清肌酐升高≥0. 5 mg/ dl見于約21%的患者。
另一項關于伴代償或失代償性肝病,且拉米夫定耐藥HBV感染患者的研究也獲得了相似結果。在繼續使用拉米夫定的基礎上加用阿德福韋,治療48周后獲得了顯著的血清HBV
DNA降低效果(4一5 log10拷貝/ml)。失代償性肝病患者的生化學參數和肝功能狀態得到顯著改善。
(2)干擾素 對于臨床上存在失代償性肝硬化的患者,IFN的應用是一個問題。雖然患者在IFN治療后顯示了應答,但治療期間肝病趨向惡化,且在結束治療后需數月才能恢復肝臟生化學的正常。此外,IFN治療存在發生嚴重并發癥的風險,包括嚴重的細菌感染和肝炎加劇。在失代償性患者,肝功能處于Child- Turcotte-Pugh A級的患者較B和C級患者能獲得更好的應答率,分別為100%、33%和0。甚至低劑量的IFN也可能在非A級的肝硬化患者引起細菌感染,提示IFN不能用于治療這些患者。IFN用于治療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看來是安全的,盡管延長治療有發生肝功能失代償的危險。尚無隨機臨床試驗對PEG-IFN在這些患者群中的應用進行評價。
(3)拉米夫定 已經證實,拉米夫定治療可延緩進展性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臨床進程。一項大型隨機安慰劑對照研究顯示,在平均治療32個月后,拉米夫定治療組7.8%的患者達到了臨床終點,而在安慰劑對照組為17.7%。此外,在減少HCC發生率方面,拉米夫定治療組也顯著優于安慰劑對照組(3.9%對7.4%)。雖然49%接受拉米夫定治療的患者出現了YMDD變異,但與安慰劑對照組相比,盡管有耐藥的發生,這些患者出現的臨床并發癥較少。因此,拉米夫定可以明顯改善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的治療結果。數個其他研究也支持這一結論。27例非肝移植的患者應用拉米夫定治療平均869 d,血清HBV DNA水平迅速下降,ALT恢復正常,部分患者獲得了HBeAg的清除,血清白蛋白和膽紅素水平也得以改善。在另一項由Villeneuve等完成的相似研究中,在拉米夫定治療超過9個月以上的患者中觀察到病情的改善。血清HBV DNA水平下降,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 和ALT恢復正常,白蛋白、凝血酶原時間及Child- Turcotte- Pugh評分等也得以改善。這兩項研究還顯示,與歷史對照相比,拉米夫定治療組的存活率得以改善。然而,拉米夫定治療6-12個月后可出現YMDD變異株,臨床表現為HBV DNA和ALT水平的升高。在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YMDD變異株與肝臟生化功能失常和效率減退相關。一些肝硬化患者不能耐受YMDD變異株,一旦出現YMDD變異,肝病可能迅速惡化。這些研究支持拉米夫定,可能還有恩替卡韋,以及阿德福韋可以有效治療繼發于HBV感染的失代償性肝硬化方面的理論。
目前關于恩替卡韋治療進展性肝病的資料有限。回顧性分析恩替卡韋Ⅲ期臨床試驗中有關肝硬化患者對治療的應答清況,結果顯示恩替卡韋的服用耐受性良好,在治療終點時的組織學改善、ALT復常、血清HBV DNA水平測不出等指標均優于拉米夫定治療組。尚無應用PEG-IFNα-2 a治療進展性肝病的資料,但應用普通IFN治療這些患者的經驗提示,對這些患者應當避免使用PEG-IFNα-2a。
2.治療建議:肝硬化患者
關于HBeAg(+)或HBeAg(-)的代償性和失代償性肝硬化的治療建議見表9和表10。對于血清HBV DNA<2000IU/ml的代償性肝硬化患者,可選擇監測,或應用恩替卡韋或阿德福韋進行治療。專家小組認為,雖然目前尚無資料來指導這一選擇,但有顯著臨床肝病(盡管是代償性肝病)的患者,應用這些藥物進行治療所具有的潛在臨床收益比藥物毒性風險和治療花費更為重要。對于血清HBV DNA≥2 000 IU/ml的患者,恩替卡韋或阿德福韋可作為第一線選擇,因為它們的療效和良好的耐受性已經得到證明。專家小組認為,雖然由于IFN可誘導肝病加重和失代償而禁忌使用,但PEG-IFNα-2a對代償性肝硬化可能具有治療價值。鑒于需要長期治療,恩替卡韋和呼阿德福韋優于拉米夫定,這是因為拉米夫定的耐藥率較高,并有可能因此而引起臨床失代償。阿德福韋與拉米夫定(或可能恩替卡韋)聯合使用,理論上可減少對其中某一藥物耐藥,或同時減少對兩種藥物耐藥。
單位為IU/ml(1IU/ml約等于5.6拷貝/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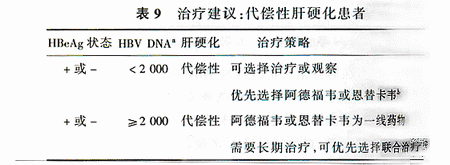
a.單位為IU/ml(1 IU/ml約等于5.6拷貝/ml)
b.雖然尚無資料可供參考,但PEG-IFNα-2a可以是肝功能代償良好的早期肝硬化的治療選擇之一。c.以拉米夫定(抑或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聯合治療,理論上具有良好的效果,因為這可能使得耐藥率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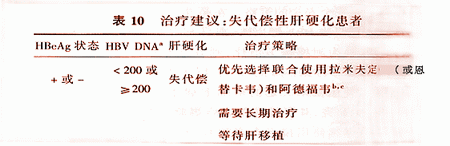
a.單位為IU/ml(1 IU/ml約等于5.6拷貝/ml)
b.目前尚無恩替卡韋的相關資料;PEG-IFNα-2a應禁止使用
c.以拉米夫定(抑或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聯合治療,理論上具有良好的效果,因為這可能使得耐藥率更低。
所有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不論其血清HBV DNA水平如何,均應考慮給予治療。阿德福韋與拉米夫定(或可能思替卡韋)聯合,是值得擇優考慮的一線藥物。對失代償性肝病患者進行治療的目的是改善其疾病狀態,例如使他們最終能從肝移植名單中移除。聯合治療可降低或推遲藥物耐藥的發生,因此,推薦使用阿德福韋與拉米夫定(或可能恩替卡韋)聯合應用作為失代償性肝功能的一線治療藥物。對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應用阿德福韋加拉米夫定,阿德福韋加恩替卡韋或其他聯合治療方案的評估研究應當是需要和合理的。
專家組認為,肝硬化患者的治療應當是長期的和無限期的。雖然并無關于對代償性肝硬化患者在HBeAg血清學轉換后繼續治療有益的資料,但來自中國的資料顯示,即使發生HBeAg血清學轉換,也仍然有可能發展為HCC或進展性肝病。這可能是由于持續存在低水平的HBV和(或)由于其他致癌因素的啟動和傳播(盡管病毒復制受到抑制)。雖然缺乏對肝硬化患者有益的資料,但鑒于核苷/核苷酸類似物優越的安全性特點,治療應當持續至患者血清HBV DNA轉陰和HBsAg消失。治療期間應當每3個月監測1次。對于有多種腎功能損害危險因素的患者,在治療前和治療中密切監測腎功能是十分重要的。藥品生產廠家應當根據建議對阿德福韋、恩替卡韋和拉米夫定等藥物的劑量頻次作出調整。
(五)HIV/HBV及HCV/HBV合并感染的患者
在美國和歐洲,約10%的HIV感染者合并感染HBV。來自多中心艾滋病的隊列研究資料[包括患者在治療前和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HAART)后的資料]顯示,HIV/HBV合并感染者與肝臟相關的病死率約為兩種病毒各自單獨感染時的14倍。有很高比例的HIV陽性患者接受拉米夫定、替諾福韋和(或)恩曲他濱治療,而這些藥物也具有抗HBV活性。
1、主要臨床資料概述
(1)阿德福韋酯 在HIV/HBV合并感染并且發生拉米夫定耐藥的患者,阿德福韋10mg/d是有效的,服藥第144周時約64%的患者出現HBV DNA下降5.45log10,ALT恢復正常。在第96周時,接受試驗的患者沒有任何一例發生對阿德福韋耐藥的HBV DNA聚合酶變異。由于阿德福韋10mg/d沒有抗HIV效果,因此阿德福韋的好處在于不會篩選出耐阿德福韋或耐替諾福韋的HIV變異株。有2例患者血清肌酐水平升高≥0.5mg/dl,同時血清無機磷沒有明顯變化,后來血清肌酐水平升高得以解決,并考慮與阿德福韋無關。
(2)恩替卡韋 新近的研究顯示,恩替卡韋治療HIV/HBV合并感染有效。一項安慰劑對照研究以恩替卡韋治療HIV/HBV合并感染的患者,服藥24周時血清HBV DNA下降了3.66log10。
(3)拉米夫定 已有研究顯示拉米夫定治療HIV/HBV合并感染的患者有效,可使血清HBV DNA顯著下降,而且耐受性良好。在HIV/HBV合并感染的患者用拉米夫定治療4年的耐藥率達90%,高于HBV單獨感染者。
(4)替諾福韋 數項研究已經證實,替諾福韋是有效的抗HIV和抗HBV藥物。Cooper等的一項研究顯示,替諾福韋治療可使HIV下降6 log10,使HBV自基線下降5 logl0。相似的是另一項對HIV/HBV合并感染的研究顯示,替諾福韋治療第24周血清HBV DNA下降了4 logl0,CD4陽性細胞約升高80。有一項小型、開放一標記、非隨機研究的對象為拉米夫定耐藥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感染有HIV,用替諾福韋或阿德福韋治療48周,結果顯示,替諾福韋組的效果優于阿德福韋組,HBV DNA載量下降幅度較大(-5.5對一2. 8 log10拷貝/ml),HBV DNA轉陰率很高(100%對44%)。但是,有資料顯示替諾福韋治療可能出現腎毒性和高磷血癥。
2.治療建議:HIV/HBV合并感染
對HIV/HBV合并感染者的治療,需要根據患者的狀態進行個性化。替諾福韋、恩替卡韋、阿德福韋均是有效的抗HBV藥物,但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沒有抗HIV活性。對于尚不需要抗HIV治療的患者,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抗HIV活性的缺乏提供了理論上的治療優勢,因為如果使HIV感染者不必要地暴露于替諾福韋或拉米夫定單獨治療的壓力下,有可能損害以后對HIV的治療。如果患者接受抗HIV治療,可選擇包含替諾福韋、替諾福韋/拉米夫定或替諾福韋/恩曲他濱的HAART方案。對于正在接受穩定的HIV治療方案的患者,宜加用阿德福韋或恩替卡韋抗HBV治療,而不是直接轉換為替諾福韋以試圖同時覆蓋打擊兩種病毒。
在HCV/HBV合并感染的患者中靜脈注射毒品者常合并感染有HCV和HBV。多方面的研究顯示HCV/HBV,聯合感染的結果較之其中任何一種病毒單獨感染都要嚴重得多。絕大多數患者往往是一種病毒感染趨于占優勢,而另一種病毒趨于休眠。在HCV占優勢的疾病,能在血清中測到HCV RNA但不能測到HBV DNA。反之,若HBV占優勢,則能在血清中測到HBV DNA但不能測及HCV RNA。許多HBV/HCV合并感染的患者趨向表現為HBeAg(-)及低水平HBV DNA,而以HCV感染占據優勢。
治療建議:HCV/HBV合并感染
對于合并感染HBV和HCV的患者,目前尚無標準的治療方案。對患者應當進行評估,判斷哪種病毒感染占優勢,然后據此給予治療。因此,如果患者血清HBV DNA≥104IU/m1,并且不能測到HCV RNA,這時應當針對HBV進行治療。然而,由于許多患者趨于表現為低水平HBV DNA但卻可測到HCV RNA,專家組建議,對HCV/HBV合并感染者,若能測到HCV RNA且有高水平的HBV DNA,則采用標準劑量的PEG- IFN和利巴韋林(病毒唑)治療3個月;若HBV DNA無應答甚或升高,則可加用恩替卡韋或阿德福韋。新近一項研究顯示,由于HCV感染占優勢而接受抗HCV治療的HCV/HBV合并感染者,其應答情況與僅有慢性HCV感染的患者一樣,只有少數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HBV感染的活化。
(六)化學治療
據報道,HBV復制的再激活(血清HBV DNA和ALT水平升高)可見于20%一50%接受免疫抑制或癌癥化療的HBsAg攜帶者。在絕大多數病例,肝炎的發作為無癥狀性,但也觀察到有黃疸性加劇甚至肝功能失代償和死亡的患者。非對照性研究顯示,與歷史對照相比,用拉米夫定進行預防性治療可減少HBV再激活的幾率、與肝炎相關的病情嚴重度及病死率。有一項研究顯示,在化療前即開始應用拉米夫定進行治療,較之在化療過程中出現HBV復制再激活的表現后才給予拉米夫定治療,前者發生的臨床肝炎較少。雖然這些研究有不少局限性,但看來可以在開始進行化療或免疫抑制治療時對HBsAg攜帶者審慎地進行預防性抗病毒,并且在其后維持抗病毒治療約3個月。對于需要終生接受免疫抑制治療的HBsAg攜帶者,例如腎移植受者,尚不能肯定預防性抗病毒治療的收益/危險比。方法之一是可以對這些患者進行監測,若出現顯著的HBV DNA和ALT水平升高,則開始抗病毒治療。雖然阿德福韋和恩替卡韋可作為替代藥物,但截止目前的資料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拉米夫定。由于預防性治療通常是短期治療,因此拉米夫定的耐藥可以較少關注。然而,如果治療很可能需要超過6個月,專家組建議使用阿德福韋或恩替卡韋替代拉米夫定。雖然HBV的再激活有可能發生于HBsAg(-)、僅有抗-HBc(+)或同時存在抗-HBc(+)和抗-HBs(+)的患者,但這些患者HBV的再激活是不常見的,此時是否需要常規進行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尚無足夠的支持信息。然而,專家組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意見存在分歧,因為部分專家已在僅有抗-HBc(+)的患者中觀察到乙型肝炎的加劇,表現為測及HBsAg以及嚴重的生化學和臨床改變。因此,對這些患者考慮給予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并非不盡合理,部分專家建議選用口服藥物對HBsAg(一)、抗-HBc(+)和(或)抗-HBs(+)的患者進行預防性治療。
(七)妊娠
拉米夫定、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被歸入C類藥品,因此,應當遵循標準的C類藥品使用建議。對妊娠婦女是否開始和(或)繼續應用抗病毒治療,應根據母親當時的肝病狀態及可能獲得的潛在利益,并適當考慮胎兒可能經受的細小風險。由于抗病毒治療最常涉及可能僅存在輕微肝病的年輕婦女,因此推遲到妊娠以后再給予抗病毒治療可能比較謹慎。雖然拉米夫定在孕婦中應用的安全性經驗遠遠多于阿德福韋和恩替卡韋,但均可使用。可以考慮在妊娠末3個月給予治療以預防HBV傳播給新生兒。雖然應用拉米夫定預防HBV傳播給新生兒有一些早期成功的報道,但也有報道提示,即使在使用拉米夫定治療、圍產期免疫預防及接種疫苗的情況下,HBV仍有可能自母親傳播給嬰幼兒。新近一項雙盲、安慰劑對照、多中心臨床試驗將144例HBsAg(+)的孕婦隨機分為接受拉米夫定100 mg/d組和安慰劑對照組,在妊娠第32周時開始治療,然后在嬰兒1歲時評價其血清HBsAg的陽性率,所有嬰兒在出生時均注射HBV免疫球蛋白(HBIG)和接種HBV疫苗。結果顯示,接受拉米夫定治療的母親所生的嬰兒發生HBV感染的幾率低于安慰劑對照組(18%對39%)。如果在妊娠期間需要治療,根據以往在HIV感染領域于婦女妊娠時應用拉米夫定的經驗,以及新近的隨機試驗結果,專家組建議將拉米夫定作為一線藥物。然而,如果需要在妊娠結束后長期治療,則可考慮在產后轉換為阿德福韋或恩替卡韋治療。任何接受拉米夫定、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治療的妊娠婦女,均應向各自的妊娠注冊單位進行匯報。
十一、耐藥監測
臨床耐藥(目前臨床中尚未常規使用基因測序法檢測耐藥)是指用2種檢測法檢測患者血清HBV DNA水平較治療時最低值升高1個log10以上(見表8)。
接受拉米夫定治療的患者,應當每3一6個月監測耐藥情況。由于阿德福韋和恩替卡韋的耐藥率顯著較低,在治療1年后可每6個月監測耐藥情況。有進展期肝病的患者,應當進行更密切的監測(即每3個月監測1次)。
十二、結論
慢性HBV感染者抗病毒治療的目的是阻止肝病進展為肝硬化和HCC。由于HBV復制影響慢性HBV感染者的臨床結局,因此抗病毒治療的首要目的是持久抑制血清HBV DNA,使之達到盡可能低的水平。PCR等分子診斷學方法的出現使得能夠準確監測低至10 IU/ml的血清HBV DNA水平,因而應當用來檢測患者在抗病毒治療前的HBV DNA基線水平,并監測抗病毒治療應答及與耐藥相關的病毒學反彈。
對HBeAg(+)的CHB患者,確定抗病毒治療對象應是HBV DNA閾值為≥20 000 IU/ml、ALT水平升高(按照修訂的正常參考范圍)和(或)肝活檢證實存在肝炎。對于ALT正常但有病毒血癥的患者,應根據個體情況需要進行肝活檢查。對這類HBV感染者需要在將來作進一步研究,因為其中有20%一25%的患者存在顯著的肝纖維化。對HBeAg(一)的CHB患者和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確定抗病毒治療對象應采取較低的HBV DNA水準。專家組推薦的閾值分別為HBV DNA≥2 000 IU/ml和≥200IU/ml。 HBeAg(一)的CHB患者和肝硬化患者需要長期抗病毒治療。阿德福韋、恩替卡韋、IFN、拉米夫定及PEG-IFNα-2a均已被批準用于CHB患者的初始抗病毒治療。然而,在選擇一個治療方案時,應當考慮這5種治療策略各自的優缺點。需要考慮的問題包括療效、安全性、耐藥、用藥方法及治療費用等。
阿德福韋在總體上與拉米夫定療效相當,并且患者的耐受性良好。其優點在于耐藥發生較遲和較少。恩替卡韋是目前最強的口服抗病毒藥物,在隨機臨床試驗中其表現優于拉米夫定。此外,在以前從未接受過抗病毒治療的患者中,恩替卡韋使用2年未發現耐藥的產生。然而,目前尚缺乏2年以上的長期療效和耐藥觀察資料。恩替卡韋和阿德福韋的治療費用均高于拉米夫定。雖然IFN和PEG-IFNα-2a具有明確的療程、相對持久的應答(在能夠產生應答的患者)和缺少耐藥,但其治療代價相對昂貴,必須通過注射給藥,并且有許多不良反應。在當前的臨床實踐中,PEG IFNα-2a有可能取代標準的IFN。拉米夫定的患者依從性良好,安全性極佳,也有較好的療效,但因易于發生耐藥而使其長期治療應用受到限制。因此,專家組不推薦將拉米夫定作為一線抗病毒藥物,除非是在化療或妊娠過程中進行短期的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在HBV/HIV合并感染者作為抗HIV治療方案的組成部分或在發生肝功能失代償的患者與阿德福韋聯合使用。對于需要治療超過1年以上的患者,可能的最佳選擇是使用阿德福韋或恩替卡韋,因為這兩者的耐藥率很低。
數個領域尚需進一步研究。聯合用藥可能被證明較單一用藥在病毒抑制方面更為有效,而且很可能降低或推遲耐藥的發生。目前正在進行幾個大型的臨床研究,以探討聯合使用2種核苷/核苷酸類抗病毒藥物,或聯合應用一種口服抗病毒藥物和PEG-IFN對代償性肝病患者的應用效果。聯合應用口服抗病毒藥物對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的治療可能尤具價值。進行聯合應用阿德福韋和拉米夫定與單用某種藥物對這類患者治療效果的比較研究,顯然是十分必要的。
幾種新的候選抗病毒藥物,如恩曲他濱、替比夫定和替諾福韋是新的潛在的治療慢性HBV感染的藥物,目前正在進行評估。這些藥物可能在未來幾年中可擴大為抗HBV治療選擇。
TAG:美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處理流程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恩替卡韋 替比夫定
相關藥品








